|

- 帖子
- 51
- 主题
- 0
- 精华
- 0
- 积分
- 715
- 威望
- 0 点
|
一米之滇——从束河到拉市,雨一直下(续)
大研古镇
(三)古城屋顶
说到古城,有一处不能不去。那就是能看得见屋顶的地方。
出了四方街,往前走过一石桥,便可登高至万古楼。万古楼是新近修建的,太人工,又要收门票,基本没多大看头。但这路上的风景不容错过。登至半山腰已没有石阶,长长一段土路上一抬眼,一大片青灰屋顶便出现在眼前,纵横交错,错落有致,一直漫延到远处的山下。尽管看不到任何的细节,你却不能否认,这片屋顶下的人脉涌动和繁衍生息。否则,屋顶也只能是屋顶而已,不会有灵魂。宪哥有首不错的歌,叫什么什么屋顶,我不太记得歌名了,如若他到此一游,恐怕会唱得更款款深情吧。
临走的前天,在阿妈家刚吃过饯别大餐,眼见已近黄昏,和颜色三步并两步急匆匆的就往后山赶,只是想再看一看落日余晖下的这一片屋顶,会散发出什么样的光彩?结果待上得狮子山来,太阳落了,山风大了,胃也疼了,光线也越来越暗了,只依稀看到丽江新城的高楼林立,和古城屋顶的一隅。我到底也没有找到小武哥常坐着发呆看夕阳漫过山坡洒向屋顶尽览无余的那个好地方,是为一遗憾也。
但是你看,掌灯了!远的近的圆的方的灯笼一盏盏亮了起来。
古城的夜,刚刚开始……
(四)纳西人
丽江是纳西文化的中心,但我们行前的预习功课做得太差,并未去了解关于这个民族的任何风俗习性,加上住的时间不长,都是初浅的接触,更谈不上熟识与深入。
慢步间,偶尔能遇到一两位穿着传统服饰的纳西妇女,对我们的拍照请求尤为害羞。因为爬坡又背着小孩,身体略微的往前倾,一步步便走远了。那小孩好奇,圆溜溜的眼睛一直扭过头来看着我们。流星语MM将镜头定格,阴的天,青的墙,灰的地,蓝花印布包着头巾的纳西族女人和背上的小孩,绝对是她堪称得意的作品。
基于这种影像,觉得本土的纳西人性情还是很腼腆,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我们听不懂,只知道简单学来的两句,“您好”叫做“wualalalei”,“谢谢”叫做“jiubeishe”。至于文字,不知是否就是东巴象形文化?
老一点的人,在衣服后片的腰间有一块白布,还经常背着大大的萝筐在街上走来走去,
吃丽江耙耙和鸡豆凉粉。但新一代的年轻人却越来越汉化了,穿酷酷的T-shit牛仔,染时尚的发色,听最新的流行乐,住新城里的洋楼,骑大油门的摩托车,跟我们在城市里的生活并没大的分别。他们大多都受过汉语教育,普通话没有京味的标准,但在我们外乡人听来,还是能相当顺畅的理解个中意思。城里也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洋人跑来开店帮工做生意,一派繁华,正因如此,很多纳西青年的英文日文说得一串的溜。
这让我想起了去年在阳朔,穷山僻壤的傍晚时分,一帮少年居然聚集在西街的某个亭台,玩起了热烈的街舞,围观的人很多,并爆发出阵阵掌声,疯狂而动感十足。
或许该庆幸为好事吧,至少说明社会文明无处不在。
相对而言,古城里的人们反而保持了更朴实无华的一面。高原强烈的日照,给了他们黝黑的皮肤,粗糙的肌理和深邃的眼睛;尽管小城的生活悠闲,但日复一日的生计也造就了他们勤劳的双手,达观的个性和好客的心灵。
在丽江认识的纳西人屈指可数,其中属客栈阿妈一家和包车的梁师傅印象最为深刻,着实让我们体会了这个民族的善良和可爱。他们的话不多但谦和,凡事尊重我们的想法,包容我们的懒散甚至放肆,晚归或者晚起了,从不说什么。
梁师傅属虎,圆圆的娃娃脸很显年轻,一看就不是张扬之人。若不是有日我们徒步完虎跳闲聊起来,任谁也猜不出他已经有了几岁大的男孩(纳西人因为肤黑的关系,少年会显得老成,而大一点的,又让你估不出大小)。早年他夫妇俩都开出租,赚了点钱盖了楼房买了小面包后,他便让妻子养生休息,自己一心一意的跑车养家,典型的勤劳致富家庭。因为价格实在,后面几天的行程,我们一直包他的车,他也就一直跟着我们跑东跑西,经常乐呵呵的在一旁看大伙打闹,偶尔也插一两句玩笑话。大家伙吃饭,通常都是饿狼扑食一扫而光,唯独他静静的坐在一边,斯斯文文的夹上些菜,三两下吃完就撤了,不愿占大家地方,可见其性之随和谦逊。即便偶尔把我们带去没什么看点的景区或是昂贵的购物处,我想也是情有可缘能够体谅的吧。真正跟他拉近距离,缘于他车上放的那些CD,都是些很不错的歌,其中还有许巍那盘《完美生活》,我喜欢,而梁师傅说,他也喜欢。有些人,如果喜欢同样的东西,至少你会在下意识里把他合并为同类项。这道理于我和梁师傅,有一半是成立的。
另有一位刚开始租他车的杨姓司机,应该有40多岁光景吧,只有小学文化,却能够跟你神侃半天,成天笑眯眯的好精神。后来因为车小人多坐不下,我们有了别的安排。结果有日在石桥上碰上,他却忘性大,问我们要不要车,直到流星语MM提醒他,才认出我们,连连和几个MM握手,邀请我们次日去参加他们的一个什么节日,还颇有些不好意思,情景之下,甚觉可爱。
人与人之间,不论民族、年龄与性别,想来是一种相当微妙的情感联系。生分还是熟悉,投缘还是陌路,全在乎你心里的感受。
只可惜我们贪玩,放弃了纳西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二月初八的“三朵节”,否则也许能见识到更多更热情更可爱的纳西人。
不过,能认识并且记住那么几个,我想已经足够了。
(五)客栈与Japanese
但凡旅游城市,客栈一定是随处可见的。街头巷尾,走两步便是一招牌,什么东巴House阿亮客栈四方客栈,大多是竖挂的灯笼或是木质的刻匾,各有各的不一样,但大都以好的景致吸引人,或做足舒适方便之文章。
寻访过古城的两家青年旅馆,都挺宽敞,庭院楼阁景物青翠的,其中一家更是眼见着干净,还配有一间不小的书吧,生着火,温暖如斯。推开后门,于水边放一套石桌躺椅,听着流水声读钟爱之作,怎一个爽字了得!
但我独爱入住的这一家。
阿妈的客栈位于偏一些的五一街上,以前取名叫香格里拉,后来因为政府管理的限制,又改为香格韵。客栈是她们原本的家,后来造访的人越来越多,便又发展成了供旅客们小住的歇息之地。
这儿虽没有四方街的热闹,也没有大石桥边的流水作伴,却是真正的纳西民居。客人和店家共处,和气相生,让人实实在在有家的感觉。
一行人中我第一个踏入客栈。迎接我的是春芽,已在这先住了好几天。她看着我直呼面熟,我一边笑言,是因为我长得太普通,一边和楼上睡眼惺忪的小狮子打招呼。谈笑间,后面的小刀、桂鱼等已鱼贯而入,猛然间多了八九人,院子里一时好不热闹。
和春芽一见如故。但她绞尽脑汁,怎么也没弄明白我同她的渊缘。后来越聊越近,终得知二人竟是十年前的校友,这才恍然大悟会心一笑。他乡遇故人,想不亲切都难。不过真正追溯起来,推荐我们过来住的,应该是阿杜。他的名头我在网上见过,签名很长说话特逗,虽然年纪比我轻,却是个老驴了。我们到的那会,这家伙睡着懒觉还没起呢。
客栈是典型的三坊一照壁式风格,入得门庭,正对着的一幢,楼下两间是主人家的客厅和卧室,楼上几间则是住客的房间,两床或三床一间,还有长长的阳台可以晾晒衣物。客厅是我们都能自由出入的,坐在沙发上聊天嗑瓜子看电视,随你的便。右侧那幢还是木板楼,踩在楼板上闷闷的响,诸红的窗格门棱,高高的门槛,一不小心便在吱嘎声中绊你两脚。倚着栏杆,便可以大声对着院子里的人说话。楼道的拐角处放着矮矮的长桌长椅,供住客休闲之用,足见主人的细心。没事的时候披了披肩,抱本书在这安静一隅发发呆,等阳光洒进来,很不错呢。
最好的地方,当属客栈的院子。贴墙种了很多花草,兰花或是别的什么不知名的植物,葱葱郁郁的显出别样的生机来。在小石头铺就的院落里,三五成群,聊聊天,喝喝茶,打打牌,上上网,不知不觉便被偷了一天。
掐指算算,我们在客栈前后住了一周左右。忙前忙后招呼我们的,是客栈的主人杨阿姨。尊崇民族化的称谓,我习惯叫她阿妈。
第一次见到阿妈,是刚到丽江的那个清晨。她的头发很短,肤如古铜,50多岁的人了,还相当勤俭,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对我们这些住客尤其热情,买菜做饭烧水,叫大家多穿衣服,帮我准备热水袋什么的,嘘寒问暖。阿妈还常为我们介绍好的风景路线,热心指点一二,或是联系价格实在的代步车辆,不单是只给我们住的地方那么简单了,周到得很。
阿妈有个二十多岁的儿子,日语说得很好,本来客栈是由他打理的,但年轻人的心志总是要远大些,不满足于在古城里做这样杂碎乍看没什么出息的事,外出工作去了,我们住的那会,就打过一次照面,也没什么印象。另有一个小女儿,在北京一间大学里学经贸类的专业,刚念到大一。家里剩下老两口,阿叔姓赵,挺高大的样子,虽也经常帮阿妈做这做那,但相对爱享清闲,这客栈里里外外的一切便落在了阿妈的肩上。也许这便是妇女的勤劳吧,做家里的主心骨,把所有事情操持得井井有条,让人佩服。
阿妈烧的菜尤其好吃,每晚一大桌子菜,一下子便被大家风卷残云扫个精光。早餐时则有热热的牛奶喝,按个人喜好,不厌其烦的为大家煮米线、买花卷、下面条,对我这样生活习性不是太好也不准时吃早餐的人来说,简直是无上的待遇了。
住客的习惯不一样,经常有人在外泡吧逛街,很晚不回来,客栈的大门,便永远为我们半虚掩着,不等大家回来,从来不上锁。待所有人都回来就寢,已经睡下的阿妈才会在寒夜里起身,披件衣服将院门从里面扣好,如此这般,未有微辞。
客栈刚请来的帮工小芳芳,才十几岁的女孩子,对我们也是热情有加。小芳芳是我们到达头一天才到阿妈家的,长得漂亮,乌黑的秀发在脑后编成又粗又长的辫子,眉眼很美,有点纳西族的乡野味道。每每说到这,她总是灿烂一辩,我是汉族人呢,然后勤快的为我们端茶倒水,跟大家没有一点生分。说起她那马上要开学的小妹,更是一脸做姐姐的自豪。那么美的笑容,那么心无芥蒂的晴朗,那么年轻的小芳芳,是客栈一并留给我的美丽记忆。
主人家好客,连小猫小狗也不例外。浅棕色毛发的小犬哈吉,和它妈妈贝贝老打架,跟我们却一点不认生,相熟得很,直往颜色MM身上钻。另外那条白色的,瞎了只眼,是阿妈捡回来的,所以起名叫多多,一幅楚楚可怜的样子,爱趴在大家伙身上找温暖。有家禽的地方,好象更显出农家生活的气息来。
客栈的冲凉房和洗手间只有一间,人一多,免不了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为此还闹出一段典故。一日发财GG拿好东西准备冲凉,见里头有声响,便问是谁?春芽有心开个玩笑,接口便道:是你最爱的人!发财GG恍然一声:我知道了,是流星语!一句话虽带点说笑意思,却字字铿锵够坦白响亮,院里同伴听来如平地惊雷,一阵爆笑,原来人家发财GG不动声色,“仰慕”流星语MM好久了。可惜当事人流星语在楼上房间并未听得真切,反倒尔后从冲凉房出来的小刀,见大家暧昧神色丈二没摸着头脑。此后很长时间,这故事便一直被大家奉为谈资,极大的提携了行走的生动指数。
这样说来,阿妈家的客栈与别处比起来,条件并不算很好,电脑上起网来也慢得让人受不了,可是有总比没有好吧。关键是住客彼此间并无陌生感,认识的不认识的,大家住在一家,吃在一家,说笑无间,没有半点拘束,如同一个大家庭,气氛相当融洽。
临走前晚,桂鱼兄他们在外边走廊玩牌,我对那东东缺乏智商,坐到客厅和阿妈阿叔聊起天来。阿妈一边与我拉着家常,一边抓起一把核桃,那么硬的东西,她牙一咬咯嘣便开了,不停的塞到我的手里,叫我多吃点,以后还要养胖点。心里润润的,一时想念起母亲,核桃也品出别样的甜来。
走的那天,在客栈门口上了梁师傅的车,透过前窗玻璃看着正与桂鱼道别的阿妈,突然有一种冲动,想要与她拥抱一次,紧紧的拥抱,不说再见。可是成长这么多年,我已经不习惯轻易流露心绪的涌动,不想被别人说成矫情,也不想让自己在感动中落泪,终于还是忍住了。
有人说,旅居途中多多少少都会感到孤独,但是阿妈的客栈,却让人感受到一种母亲般的温暖。这种温暖不光打动了我们,也吸引了不少异邦的青年特别是日本人到丽江来,到客栈来,不慌不忙一呆就是十天半个月,小石亮便是其中一个。
同大多数国人一样,我对日本人其实没多大好感,不过也犯不着象仇人似的对人家。特别是对小石亮这样憨得可爱的男生,你都没脾气了。他的日本名字按音译应该叫“Toudiu”,在我们入住客栈时,已经在那呆了一星期。刚开始见他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穿着拖鞋,带着毛线帽,模样还挺俊秀,偶尔弄两瓶小酒喝喝,看到我们总是很有礼貌的微笑,但就是不太说话,估摸着就是日本人。有时候我们玩过一两天回来,不见他,也不知一个人到哪闲逛去了,便挺佩服他们这种一个人跑到异国他乡行走的勇气。就象后几天来的叫镰田幸作的日本帅哥,居然远离家乡特地跑到北京学汉语,一学便是两年。这样学习异邦文化的决心,不是随随便便谁都能够有的。
第一次和小石亮的聊天很客气,两个人的英文都半生不熟,只好连说带比划,勉强能懂对方的意思。自此,友谊才算正式缔结。小石亮显然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有时会拿本汉语书很认真的看半天;看我和颜色用阿妈家半自动洗衣机忙得团团转,他坐在一旁偷着乐,没几分钟,便跑过来帮忙端水,也不怕鞋被浅湿;见我上网,还会调皮的凑过来说屏幕上的女孩“可爱”,用那种日本人特有的语言和腔调,让人忍俊不禁。
一晚颜色和阿杜陪我去修相机,结果见他二人忙着拍PP,不忍搅人家兴致,又恐维修店打佯,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恰巧小石亮路过,见状欣然陪我前往,走了好几条街还说自己有空,不烦,且谈兴渐浓,实在好脾气。他提起自己四年前曾经会说中国话,不过现在忘记了,并说他在古城呆段时间后便会去泰国工作。我当时并未多想,事后经颜色MM提醒才悟过来,原来他以前的女友是中国人,怪不得小石亮道来时若有所失的样子。如此跨国恋情,居然没有被我挖掘出来,可惜了一段小说素材。一路叽哩呱啦,对我的不明就理,他居然会翻出随身的日常用语互译本指给我看,待回到客栈,我已经成了他的Chinese Teacher。
从中甸回到丽江那天,正好是小石亮的生日。阿妈为他买了个大蛋糕,我们这一群人则在旁为他庆祝,桂鱼兄跑过去偷偷在他脸上抹了些奶油,结果他索性把奶油涂得满脸都是,乐呵呵的一直笑。这一天,他27岁。
这就是可爱的小石亮,他说他会记得我的姓,用日语读成“Xia”,不知道过几年,我还会不会记得,这个憨憨的日本学生呢?
待续……(好几天没写了,惭愧惭愧)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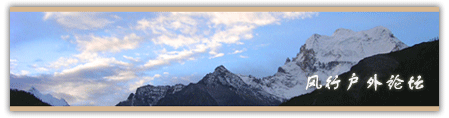


 发表于 2004-3-10 05:18
|
发表于 2004-3-10 05:18
|